当我想起他的做为,直觉告诉我,若我为他弹奏,那结局必定是我们和谐的友谊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他家我是一个记者,一个Juiliard的教授,一个钢琴文化和经验的爱好者.霍洛维兹需要我因为他把我定位为一个稍年轻的音乐知己,更重要的是,他喜欢谈论音乐和钢琴.
我早期采访时有一次谈话结束后,霍洛维兹夫人对我说:”常来,他需要你.”我感觉到这是真的,在那几年里,霍洛维兹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好朋友,而我的意义就在于和他谈论肖邦和李斯特.在我看来,在他家我能帮助他继续走下去.
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生化学反应,彼此融合.我们的强烈感情也包括霍洛维兹夫人的,若非她默许我对于她丈夫算得上是个好友,而后的多次访问只能是空中楼阁了.我欠她挺多的.
在夜访中,大部分时间他很松弛也挺兴高采烈.我见过他喝汤的样子,短领下有折好的餐巾,双目紧闭,品尝汤时倾注的注意力就像他已经进入了Scriabin奏鸣曲那和谐却错综复杂的世界.
我走进房间,嗅到那充满感情的空气.当吻过霍洛维兹夫人的手后, 她总会有一番戏剧化的举动.我能够让霍洛维兹相信他练习曲子勿庸置疑是这个星球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
相反,他们让我就从艺术的堕落到人口膨胀带来的危机中任何话题针砭时弊,发泄不快.他们乐意听我在Voltaire或阐述伦理道德的作品上高谈阔论,我也爱对钢琴的诞生进行大事挥泻.他们是很棒的听众.霍洛维兹爱说”杜勃尔先生,比起你来我可真普通.”
我会上前,坐下问他:“Maesto,你研究过Kalkbrenner的练习曲没有.”Kalkbrenner是19世纪初钢琴演奏领域对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一员。接着我们的话题马上就转到了Kalkbrenner上。
“你知道”,霍洛维兹说,“因为他的夸大,几乎每个人都笑话他。”
我接着说:“但我欣赏Kalkbrenner曾给他学生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对键盘一窍不通,那上帝赐予我们手腕有什么作用呢?’”
霍洛维兹说:“我认为他是对的,你能想象Kalkbrenner曾对肖邦说只有再跟着他学习三年才能成为完美的钢琴家吗?这对肖邦是个多么大的打击呀!”
“而且,霍洛维兹先生,那个时候21岁的肖邦已完成了练习曲创作,这些曲子的独创在钢琴技巧方面有着翻天覆地的突破呀。”
霍洛维兹继续道:“但你知道,肖邦拒绝了。不过Kalkbrenner之后继续开辟自己的天地,他没有缄默。肖邦后来也奉献给他E小调协奏曲以此来抚平他的伤痕。“
“是啊,”我接着说“肖邦一直把自己的职业经营得很好,Kalkbrenner却没有一首曲子成为保留曲目。”
这时霍洛维兹有些困难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还做了个鬼脸:“看看Kalkbrenner在我这儿还有影子没?”让我非常吃惊的是,这位主人竟能如此完美地演奏Kalkbrenner的练习曲。后来他看着我大声说道:“我在十一二岁时就学习了这些练习曲,很多年没弹了。”
“但,这么多年都没练习,你怎么还能演奏得如此完美?”
霍洛维兹谦虚地笑笑,非常随意地说:“我学得好呀。”霍洛维兹从不会停下来用这些高难度技巧来吓唬我。
名利及早就降临在霍洛维兹身上,并且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他演奏得越少,人们就越想听到他的演奏。他是大众的宠儿。霍洛维兹有着大多数人从未想到的荒唐的行为,他在旅行期间对食宿的要求和他许多古怪的行为一样是常人不可想象的。
霍洛维兹也挺自恋,但我认为从他的立场看,因为那激发旺盛的超能力,自我陶醉是必要的。那些对他很敏感的人,尤其是他妻子,对于这一点完全理解。让霍洛维兹不断地演奏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责任。
Aldous写道:“一个有些神经质的成功的艺术家,都必须得战胜巨大的困难,尽管他神经质但他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成功不是靠他的神经质得到的。“
霍洛维兹常常在自我挣扎,那时一场他曾经进行了多年的战役。偶尔会赢,不过最后在他后来几年中,他真正取得了精神上的进展。他生命中天赐的那对艺术的爱和音乐才华上的力量需要一种永不停止的尘世中的表现。
霍洛维兹在85岁时告诉我:“我说生命是不是有些短暂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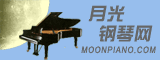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7-29 0:39:20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7-29 0:39:20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7-29 0:44:29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7-29 0:44:29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7-29 1:32:11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7-29 1:32:11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8-1 9:14:27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8-1 9:14:27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8-2 0:48:36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8-2 0:48:36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8-2 0:57:25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8-2 0:57:25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8-2 9:47:26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8-2 9:47:26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8-2 12:47:43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8-2 12:47:43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8-2 12:48:55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8-2 12:48:55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8-3 8:31:34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5-8-3 8:31:34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