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说过:音乐比文字更有力;音乐和文字结婚就是王子与乞儿结婚。也许音乐和文字本不应该放在一起作比较,毕竟无人敢说他同时十分了解文字和音乐。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每位作曲家道出的“语言”都是不同的,只因为人性中有些不约而同的特征,音乐才能流传,成了朦胧的语言。而文字则是非常清晰,不管用何种修辞手法,蕴涵多少层意思,最终也会在不久之后被解读,即使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绞尽脑汁含蓄地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作品传到朝廷也被聪明人一眼识破。不管是优秀的音乐作品,还是文学作品,都倾注了创作者最真挚的感情。所以无所谓诗人比不上作曲家优秀,解读本身也是一种亵渎,当诗歌被解读后,即使我们无比赞叹诗人的才华,但诗歌本身的美已经逊色了。音乐被认为更美,也许就是因为它永远无法被彻底解读,除非拥有了创作者的灵魂。
同是情感的容器,只要我们稍微接触这二者,便能找到一些共同之处。杜甫的诗沉郁顿挫,并且每字都炼到近乎完美。通常当我们抛开对文字的理解,凭借语感诵读第一遍,便能大致领略到老杜的情感。“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峡”和“阳”的重复正像是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OP23 NO5开头切分音的重复。从第一遍诵读,读者就能领略到杜甫欣喜的感情,原来是朝廷收蓟南蓟北。在《哀江头》中,老杜吟咏“春日潜行曲江曲”,初读时便感觉这是幽咽之声,缘于“曲江曲”的回环。拉赫在OP23 NO6和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中,也多处用回环的旋律,先是感觉“还没完”,后来便是涟漪般的愁绪缓缓而生。杜甫娓娓道出了长安沦陷,独自潜行在昔日唐玄宗与杨玉环游玩的地方,岂一个“愁”字了得?跨越千百年,相隔数万里,沉郁的杜甫跟感情极丰富的拉赫却在使用音韵表达感情上“心灵相通”。每当我诵读杜甫的诗,耳边总会响起拉赫的某段旋律,这种照应之前在我脑子里是从未经过整理的,
杜甫用表现手法表达内涵也极妙。当对面写“今夜鄜州夜,闺中只读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时,情感是很复杂的。妻子对杜甫的担忧,年幼子女无法分担这份忧愁,却增加了她内心的惆怅。而“独看”又与结尾处的“双照”呼应,暗示以前或以后有“双看”。绵绵的愁绪,化为文字意思的多重性,使读者沿着这条多支路的逶迤小道深入了杜甫哀思,与他同哀拉赫音乐的结构,何曾不是这样?如《帕格尼尼王题狂想曲》,多层次,多主题的变化,分别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而杜甫的《剑外收蓟南蓟北》,读者则能直达诗人的感情——这种大喜事,一定要迫不急待地让大家同乐。音乐与诗歌表达的层次,也与情感密不可分。
提及艺术作品的感情,不妨看看它们的流派。李白是唐诗浪漫派的代表,这里的浪漫主要是与现实相对,在创作品多采用联想、夸张等手法,语言绮丽,清新。“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天台四万八千尺,对此欲倒东南倾,”诸如此类诗句,总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许多人喜欢李白是因为对他的才华极崇拜。音乐的“浪漫”一词来源于文学,但跟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是不相干的,不过既然是浪漫,它们都不约而同带着超越现实的色彩。浪漫派作曲家的音乐总是令人陶醉,浪漫中透出更人性的内涵。通常把拉赫视为浪漫派最后的一座高峰,我想这跟科技的发展使某些幻想变为现实或破灭有关。当初由于战争和交通不便带来对故土和亲人的无限思念;与友人的一次相别通常便是永别;古代诗歌中对上天的殿堂、天地的锅炉、月中的嫦娥的幻想……都一一被现实取代,以至有些幻想在现在看来非常幼稚,这方面诗歌与音乐又是一样的。
音乐在20世纪的发展变得更绚丽。管弦乐走向了现代派的天地。肖斯塔科维奇,魏因贝格等作品家的作品的视角转向了战争、民生政治。另一方面,斯特拉文斯基、斯克里亚宾则走进神秘的人类内心世界。当中国处于黑暗中时,闻一多的《死水》、叶挺的《囚歌》点亮了一盏盏明灯,《雨巷》《断章》乃至舒婷、顾城的朦胧诗,又敞开了一扇扇新的窗户。诗歌与音乐似乎靠得更近了,我们已从隐隐觉察到它们的联系,到看见它们形影不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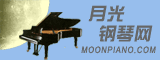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6-3-4 18:03:04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6-3-4 18:03:04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