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肯定是先有叶甫图申科的诗再有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从下面的文章可以看到,先是肖斯塔科维奇看到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并请诗人专门为交响曲第4乐章再创作一首诗,然后肖斯塔科维奇才谱曲的。
[转贴]在赫鲁晓夫时代赢得喝彩并被谱成一部交响曲的诗
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是后斯大林时期最受欢迎的诗人,五首构成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第十三交响曲(《娘子谷babi yar》)基础的诗歌的作者。叶甫图申科于2000年11月20日在波士顿大学交响乐团(Boston University Symphony Orchestra)的交响大厅(Symphony Hall)演出这部作品时发表演讲。他在纽约也通过电话周刊名“B.U. Bridge”谈了这首标题诗歌和交响曲的创作过程。
当诗人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参观娘子谷大屠杀遗址的时候使他感到震惊的并不是他所看到的东西,而是他没有看到的东西。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他就听说了纳粹在乌克兰城市基辅(Kiev)城外的大屠杀。如今,1961年,他正站在这个峡谷的悬崖上。
“我去基辅举办一场我的诗歌的朗诵会,”叶甫图申科说:“我的同伴和向导是作家阿那托利·库茨涅特索夫(Anatoli Kuznetsov),他是一切曾经发生的事情的见证人。库茨涅特索夫描述了德国人在1941年9月对大约34,000犹太人的残忍的大屠杀,以及这个峡谷是怎样被死者和伤者的躯体堆满的。
“我感到相当的羞愧,” 叶甫图申科说:“这里甚至连一个小小的标志都没有。我指的不是纪念碑,而仅仅指的是一个记载这里埋葬着数万名无辜的牺牲者的牌示。”更糟糕的是,“整个峡谷堆满了**。这里已经变成一个**堆存处了。”
自暴行发生已经过去20年了,娘子谷也已经被掩盖——文学上是这样,叶甫图申科所顺道访问的峡谷本身也是这样。
他说,有一个保持缄默的密约。因为纳粹在战时得到了热心的乌克兰合作者的帮助,另外战后斯大林正在准备他自己的对犹太人的袭击,苏维埃当权者可不想让这个题目成为比符号更多的东西。
“我在夜里写了这首诗‘娘子谷’,”叶甫图申科说:“大概花了三四个小时。我立刻打电话给莫斯科的一个朋友并向他朗诵了这首诗。但我忘记了我的电话是能够被窃听的。”
第二天上午,官方把叶甫图申科诗歌朗诵会的宣传牌全拆掉了。当他要求说明诗歌朗诵会被取消的理由时,“官僚告诉我这里正爆发流感。我懂他们的意思。所以我敲诈(blackmail)他们。”
怎么做?
“哈!这很容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者丛林中的猴子(monkeys in the socialist jungle)。
“我知道怎么做。我们[威胁]说这会制造一个丑闻。既然人们应该忘掉关于娘子谷的事情,官僚当然害怕唤醒他们的记忆。他们不说那是因为我的诗,但是我明白,就是这么回事。”
可憎的恐怖
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在《大屠杀》(The Holocaust)(1985)中写道:“娘子谷的恐怖是无止境的和可憎的。”德国于1941年9月19日占领了基辅,并在一周后命令这个城市剩余的犹太人(主要是妇女,小孩和老人),像军队中的男人一样集合并被重新安置。他引用了一个目击者的证词,里面描写了乌克兰警察是怎样“形成一个通道并驱赶着惊慌失措的人们朝着巨大的林间空地走去。到了那里以后,用棍子,咒骂和撕咬人身体的狗强迫人们脱光衣服,按每百人集合成一个纵队。接着一个纵队一个纵队的排成两列向峡谷嘴走去。
“……他们发现他们站在[娘子谷]悬崖上方的一个很窄的地方,大约20-25米高,他们的对面是德国人的机械枪。死者,伤者和快死的的人一一倒下,跌入谷中并摔得粉碎。然后下一个一百人被带来,剩下的一切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警察抓起小孩的腿把他们活活的扔入谷中。
“……德国人破坏了峡谷的崖壁,把人们埋葬在厚厚的土堆之中。然而很久以后土堆仍然在动,因为受伤的和将死的犹太人仍然在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娘子谷成为了数万名犹太人,吉普赛人和苏维埃战犯的坟墓。据苏联估计,这里可能处死了10万人。大屠杀,除去乌克兰通敌者参与的细节以外,成为一个反映法西斯罪恶的有用的苏维埃象征和一个避免谈及诸如斯大林的清洗和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之类的苏维埃罪恶的简单的途径。
危险的诗篇
朗诵这首诗是一回事,出版它是另一回事。当1961年9月这首诗出现在有巨大影响力的报纸《文学报》(Literaturnaya Gazeta)(其发行量以百万计)时,苏维埃当权者开始对叶甫图申科施加压力。“出版这首诗是编辑瓦列里·库索拉波夫(Valeri Kosolapov)的一项非常勇敢的决定,”叶甫图申科说:“他是一个老兵,这点很有帮助,因为当年他随着红军进入基辅城。红军发现这座巨大的墓地时他目睹了这一切。库索拉波夫说他和他的妻子不得不考虑这个决定,我问,为什么?他说:‘如果出版它的话我会被解雇。’”
叶甫图申科一直等到“深夜”。编辑的妻子出来,“这时她的眼睛有一点湿润,她对我说,‘我们决定被解雇。’”
在娘子谷没有立下纪念碑,
那悬崖绝壁就象一座粗糙的墓碑。
我心中恐惧。
犹太民族的年岁,
也正是我今天的年岁。
叶甫图申科解释说他陷入麻烦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诗仅仅是附带提及了发生在娘子谷的大屠杀,而在更广的层面上猛烈抨击了反犹主义。“当权者想停止这首诗的演出”,叶甫图申科说:“许多文章谴责我在这首诗中仅仅反映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而没有提及那里也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牺牲者。这首诗提到了娘子谷,但它并不是一篇严谨的评论或者调查报告,而是一首隐喻的诗。”
鲜血直流,流淌一地。
小酒馆的首领横行霸道,
浑身是烧酒和大蘸的气味。
我无力反抗,被皮靴踢倒。
我哀求暴徒也是徒劳。
他们哈哈大笑
“打死犹太人拯救俄罗斯!”
一个粮商殴打我的母亲。
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当时生活在苏联的最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从《文学报》上读了《娘子谷》。他向叶甫图申科询问他是否可以将这首诗谱成音乐。
“他在我被许多方面攻击时将我唤醒”,叶甫图申科说:“就像上帝从天堂发出的召唤一样。我记得我们在战时是怎样收听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Leningrad Symphony )[第七交响曲,作于1942年]的。在我的故乡,济马站(Zima Junction )[位于西伯利亚],我们的学校或者家里都没有广播。那里非常的冷,但是工人,妇女和小孩组成了庞大的人群聚集在户外通过电杆上的黑色喇叭收听这部交响曲。列宁格勒在战时真的是鼓舞人心。”
虽然肖斯塔科维奇向叶甫图申科询问了将这首诗谱成音乐的许可,但他当时显然已经完成谱曲工作了。叶甫图申科回忆说:“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在那里他边弹边唱。”作曲家没用多久又将另外三首诗谱成曲,并要求诗人为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写一首诗。肖斯塔科维奇的原始构思是用一套声乐组曲来构成他的第十三交响曲的五个乐章,每一个乐章是一首诗:《娘子谷》(Babi Yar),《幽默》(Humor),《在店里》(In the Store),《恐怖》(Fears)和《追名逐利》(A Career)。诗歌由一个男声合唱团和一位低音独唱者演唱。
“在我听来他们棒极了”,叶甫图申科说:“在一部交响曲中他把没人想象能够联系起来的主题联系起来了,就像莎士比亚的高低风格(high and low styles):人们在娘子谷乐章中哭泣,在幽默和追名逐利乐章中欢笑。
第一次演出或者最后一次演出
叶甫图申科的诗仍然令直至赫鲁晓夫的苏维埃当权者苦恼,这危害到了这部交响曲预定在1962年11月18日的首演。“他们不能直接的表示他们的谴责”,叶甫图申科说:“所以他们把这些谴责隐藏在俄罗斯爱国心的面具之下,控诉我侮辱了俄罗斯人民的感情。老天有眼,在我那一代的俄罗斯人中恐怕没有谁比我写了更多的作品反映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由于战争而受到的伤害。他们组织了一个[反对我]的信函运动,这做起来相当容易。”
首演前的公开排练是如此的惊心动魄,以至于倾向于中止整个事件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关键的音乐家们施压,要他们退出演出。“演出前的气氛很糟糕,因为指挥在最后一刻拒绝[参加];来自基辅的独唱,鲍里斯·格梅里亚(Boris Gmyria),在乌克兰共产党的压力之下也拒绝[演出]。他们背叛了肖斯塔科维奇。”
基里尔·康德拉申(Kirill Kondrashin)同意指挥,肖斯塔科维奇也找到了另一个独唱者——但他最终没能出现,事实上是他的替补演员演唱的。“首演是一个政治和社会事件”,叶甫图申科说:“大约有40分钟的起立鼓掌。音乐会大厅外的交通已经瘫痪了,因为人们已经知道我的诗。所有人都很惊讶演出竟然被许可了。”
但是当时的官员准备把首演变成最后一次演出。叶甫图申科说:“他们对康德拉申下了最后通牒:‘人们都义愤填膺,如果叶甫图申科不能提到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也和犹太人一样被杀害的话,我们不会批准以后的演出。’”
“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个体谅的人。他没有强迫我去做这件事,他一个字也没有说。我写了艺术上不需要的诗句,那些诗句绝对不会改变这首诗的含义。这是一个战术步骤。”
这里埋葬的尸体成千上万,
面对他们的荒冢我也发出
无休无止的无声呼唤。
向每一个被枪杀的婴儿,
向每一个被枪杀的老人。
被改成
我想到俄罗斯的功勋,
她以自己的身躯阻挡住法西斯的进程,
她的每一颗最小最小的露珠,
都贴着我的心,
联着我的命运。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叶甫图申科说:“我写了这些诗句是为了保住这部交响曲,我是对的。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一部伟大的杰作可能就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今天,这首诗被广泛的翻译和编成选集。同时,在这部交响曲每一次演出时被演唱,用的是它原来的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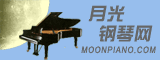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Post By:2005-8-13 11:54:3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8-13 11:54:32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Post By:2005-8-13 12:13:1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8-13 12:13:18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Post By:2005-8-13 12:16:5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8-13 12:16:53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Post By:2005-8-13 12:18:0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8-13 12:18:05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8-13 16:10:2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8-13 16:10:23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
 Post By:2005-8-13 21:56:2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8-13 21:56:29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