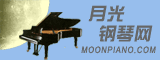|
布伦德尔是20世纪德奥钢琴学派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他的演奏风格继承德奥体系的传统,注重乐曲结构和内在张力,以广博的知识、高超的技艺、丰富的想象力而见长。善于处理装饰音和华彩乐段,音色变化细腻,情感丰富深邃,对所品的诠释深刻完美,充分表现出“学者型”钢琴家的艺术特色。
布伦德尔的演奏深受菲舍尔-迪斯考的影响,早期以演奏李斯特的作品名噪一时,后期对舒伯特的作品有独到的演绎,被认为是当今最权威的舒伯特作品演奏专家。他演奏的舒伯特奏鸣曲自然是权威的诠释,他与克利夫兰四重奏团录制的《鳟鱼》是此曲最平衡的版本。此外,他演奏的贝多芬32首奏鸣曲也受乐坛好评。《乐思与回想》是他一生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音乐艺术的又一贡献。
自述
芝加号的七月,天气闷热而潮湿。本地人和外来人都快步疾走,一心只想赶快钻进有空调的地方躲避暑热。人们无疑会认为:一位来这里访问的艺术大师,此刻一定在他下榻的宾馆中舒舒服服地休息。但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却不是这样。身穿蓝色牛仔裤和开领衬衫,这位身材瘦长的钢琴家正在拉文尼亚公国默雷剧院的后台小息片刻。他脸上显露出疲惫,前额布满无数汗珠。他刚刚完成连续几小时的练习。在即将开始的演奏会上,他要弹奏三首贝多芬的小协奏曲。即使是在气温凉爽的环境里,这也不能不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一当谈起自己的艺术生涯,谈起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对钢琴的偏好,挂在这位艺术大师脸上的倦意便像一层皮壳一样地脱落了。
只是我大约十七或十八岁左右,我才决定以钢琴演奏作我的终生职业。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同时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我六岁便开始学钢琴,但随着年岁稍长,我也搞过作曲、绘画,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当然也写过诗。因此,我面前似乎有多条道路可走。但后来我决定看看我在钢琴上究竟能够做出些什么。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随着我不断前进,我越来越看出:钢琴是一种应该不断超越自身的乐器。与人的声音和弦乐器的声音相比,钢琴的声音并不是那么独特地富于个性。它没有它们所具有的那种直接的感官上的呼求。它有待转变为某种别的东西,有待扮演一个角色。它应该发出任何别的乐器的声音,就是不要发出钢琴自己的声音。它应该是一个管弦乐队,或者,应该是一个人的歌喉发出的声音。它应该歌唱是因为歌唱在音乐中始终是十分重要的。钢琴能够而且应该唤起别的世界的声音,但它不应该像一架钢琴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不是一个禀赋特异的孩子,我16岁之后就没有自己的私人老师。我仅仅是去听一些大师们的讲课。在这些课程中,埃德温·费肖尔(EdwinFischer)的课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我不得不自己摸索出许多东西以使这种影响缓慢地,但却完全彻底地成为我自己的一个过程。首先,我学会了将每一篇大师的作品看作是二个自足的实体。你必须弄清为什么一部作品是如此地不同和独特于其它作品,而不是要去弄清它为什么类似于某部作品。
其次,我总是尽可能素朴而自然地去看每一部作品,而不是一开始就试图分析它。我既然知道作曲的过程,便认为这种分析应该是在与作品成为熟悉的朋友之后,而不是事先就强行把某种见解输入到作品中去。我越是长时间地弹奏乐曲,就越来越懂得这些乐曲。但我仍然尽量保持一种素朴天然的态度。是否对音乐家而言情感比思想更为重要?我在我的著作《音乐的思考与后思考》(MusicalThoughtsandAftrth-oughts)中这样写过:“尽管我十分欣赏思考,但我发现情感对音乐家更为重要。情感贯彻始终,它既是音乐由以开始的起点又是其不得不返回的归宿。”这并不表明我没有给思考以极高的估价。事实上,我比许多人都更加看重思考的作用。因为这是一种批评的作用,它针对的是音乐家及其音乐的性质——音乐家不应该是“理智的”,否则,音乐的魔力和符咒就会荡然无存。毕竟,许多人更喜欢音乐显得像是某种从天上降临下来的东西。
任何人只要多年来一直与大师级的音乐作品生活在一起,慢慢体味它们的内涵和结构,体味各种主题是如何在一个乐章中和谐一致的,各个乐章又是如何在一部奏鸣曲中和谐一致的,他就会发现:贝多芬的奏鸣曲是理智的一项惊人伟绩,而这种思理(intellectuality)已成为整个奏鸣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与情感交溶在一起。这的确是混沌和秩序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按照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的说法,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混沌必须透过秩序的装饰照射出来。”没有秩序,也就没有艺术作品。如果混沌是包围着我们的生活,艺术就是创造出与之对抗的秩序的东西。因此在我看来,艺术与生活是正相反的东西,它们并不一定是彼此的镜子。正因为如此,许多艺术家的内心才完全不同于他的外在表现。
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我知道是音乐在向你发布命令。它告诉你手指如何动作,踏瓣如何使用,双手如何运动。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相信在练习时应该故意放慢节拍这种说法的缘故。如果我延缓乐曲的过程,指法也许会出错,两手的动作也许会达不到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放慢节拍来发现正确的指法,以至把一首本来快速的乐曲弹奏得很慢,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爱德华.斯图尔曼(Edwardsteu-ermann)教学中最令我敬佩的便是:他总是让他的学生用快速的节拍学习一段乐曲,但他将这段乐曲分成若干小段。他告诉学生以特定的方式将乐曲弹奏到某一处。尔后,他又要求学生弹奏第二小段并使之与第一小段衔接起来。这样继续下去一直到学生完成了整部作品。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不允许学生放慢速度。这种体系很可能也有利于记住整部作品。由于某种缘故,我从未有过记忆上的困难。通常,一部作品弹奏几遍后,它便被打进了我的头脑。在演奏中如果我偶尔发生记忆上的差错,那也更可能发生在独奏音乐会上,而不是发生在有乐队伴奏的时候。我总是力图如大多数艺术家那样摆脱记忆上的差错。埃德温·费肖尔、阿尔弗雷德·柯托、阿图尔·施纳贝尔都承认他们偶有记忆上的失误,但他们却仍然是最伟大的钢琴家。我不相信他们中会有任何人愿意故意放慢一首乐曲的速度。以此来避免其在必需的弹奏速度下可能冒的技术风险。
为了使自己在钢琴上继续取得进展,我常听阿瑟·鲁宾斯坦(ArthurRubinstein)和威廉·肯普夫(WilhelmKempff)的演奏。我很有兴趣听我的年轻同行们的演奏,但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回过头去听费肖尔、科托以及斯纳贝尔的录音。实际上.我对指挥家和歌唱家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在他们那里有许多可学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我喜欢听贝多芬和李斯特弹奏。我认为李斯特一定比今天所有的钢琴家更优秀。他一定能在音乐上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你只要看看他年轻时写的那些东西,例如那些最难的练习曲如十二首超技练习曲(etudesd’executiontranscendante)。你不能想象今天有任何人能在技巧上比他更好。也许有些人能够较少地弹错音符,但那又怎样呢?并不能表明他们就更伟大。我愿意亲自见见舒曼、贝多芬、莫扎特。莫扎特或许是最有趣的人,因为很难想象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认为有谁弄清了这一点。我希望继续走向成熟,我还只是40出头,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尽管总地说来我对评论家的评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有一次在纽约,一位评论家暗示说:我所弹奏的贝多芬将在未来几年中走向成熟。我希望这位评论家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一直在从贝多芬的作品中发现新的微妙之处。新的发现必须一直继续下去。如果我认为我已穷尽了整个贝多芬,我想这将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他的作品是那样惊人的复杂,新的洞察和发现简直没有尽头。我不需要批评家来告诉我这一点。艺术家必须做的一件事是保持自己个人的判断力。他不应该太多地受批评家的影响。有时候批评家说的话可能是正确的,但这通常是在音乐会的演出效果方面。如果我得到的印象是我弹奏得不好,那往往是场地在传达音响效果方面的原因。例如,我在台上听见的声音可能极大地不同于人们在观众席上听见的声音,而这将改变整个演出的形象,正像你在不同的功放器和喇叭箱上放一张同样的唱片,其效果可能发生极大的改变一样。有时候同一张唱片可能产生出不同的、令人失望的效果。在整个传输渠道的某一个地方,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可能会失落。因此在演奏过程中我不得不不断地向自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演奏在听众席上产生的效果怎样?他们听见了些什么?”
因此当你问到我的成功,以及任何艺术家取得的成功所具有的性质,我能够回答的只是指出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并承认成功的性质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显然,我没有早期的成功可谈论。当我25岁的时候,我不属于那种在体格上就能广泛赢得公众的人。我的确属于局外人,而我也希望做一个局外人。我用某种嘲讽、鄙视的眼光去看待公众,在那些年代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设计自己。我试图自己独自做成一切事情,这使我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找到自己的事业。但这一过程也有某些好处,它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我的音乐修养,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人、了解人。我能够轻松悠闲地研究音乐演奏会的种种事实井观察这架机器如何运转,我对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将不得不怎样树立自己的形象也有了更好的观察和透视。我有幸没有处在必须设法维持早期取得的成功的巨大压力下,那种压力甚至可以使最大的才能遭到毁灭。我并不认为有什么成功秘诀,如果真有什么秘诀,我知道我并没有遵循它。
未来会发生些什么,这对我无疑也像对别的任何人一样难以预言。我知道我并不希望成为一名指挥家,我对指挥之所以有极大的兴趣是因为它能告诉我钢琴家应尽量避免哪些速度和节拍上的变化和更改——它们是无法指挥的。我经常在自己心中指挥,而我的指挥也将到此为止。当然冲突不会总是演奏者和指挥家就一部特定的作品如何演奏而产生不同的看法。有时候,那是技巧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则是年龄差异或人格个性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得不作出妥协,以获得即使不是最理想的,至少也是可能取得的最佳效果。例如有时候,指挥家认为一部作品应该以不同的速度来弹奏。我试图说服他同意我对该作品的看法,但我的看法或许不能令他信服,这仅仅因为他不能像我那样去感受这部作品而已。有时候也涉及到技术性问题。例如贝多芬第一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认为这里应该进行得很快,只有以很快的四拍才能使它有意义。然而,打出很快的四拍对某些指挥家来说却是不能熟练做到的事情。如果他们以快二拍(allabreve)开始,这首乐曲听上去便大异其趣了。它不再是它应该是的样子——第一拍和第三拍略微得以强调,第二拍和第四拍稍稍受到忽略。同样,勃拉姆斯的D小调协奏曲甚至对最有经验的指挥家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障碍,因为,第一乐章的节拍恰恰在六拍和快二拍之间。指挥家若打六拍,这一乐章便可能变得太慢;而如果他打快二拍,它又可能变得太快。
我要说大多数指挥家根据其对于钢琴演奏家的尊敬,总是竭力采取合作态度的。指挥家们尊敬那些懂得整部作品,而不是仅仅懂得其不得不弹奏的音符的钢琴演奏家。问题出在某些年龄较大的指挥家身上,这或者因为他们不认为有必要反复排演,或者因为他们只想我行我素。一旦某位指挥家年逾七旬,再与他讨论就没有什么好处了。此时钢琴演奏者最好下定决心索性为乐队伴奏。对此,我很少发现有什么例外。阿德里安·波尔蒂(AdrianBoult)在这方面是素负盛名的一位。指挥家不得不保持他凌驾于乐队之上的权威。如果他感到不安全,他会把钢琴演奏者视为挑战者,而整个演奏会听上去就会像一个人试图获得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一样。克劳迪欧.阿巴多(ClaudioAbbada)、丹尼尔.巴伦波因(DanielBarenboim)和吉米.李维尼(JimmyLevlne)是我喜欢与之一起工作的指挥家中的几位,因为他们懂得我想要什么。另一位指挥家是大卫·津曼(DavidZinman),我希望他很快会成为著名指挥家,因为他完全配得上成为著名指挥家。
我并不热衷于教学生,尽管我想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位举办演奏会的钢琴艺术家做自己的老师。我并非没有做过这种事,我做过。有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一种是用很长一段时间培养一名学生,对他负完全责任,不仅在音乐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对他负责。这样,教师便成为学生的密友和知己,成为他的激励者,成为他或爱或恨的对象。另一种方式是办高级班(masterclasses),即在教学中与学生发生短暂的接触,而在接触过程中,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作品。我从未感到自已有经常从事有规律的教学活动的冲动和愿望。但另一方面,高级班却使我感到愉快。当然,这要取决于参与者的水平。在那里,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出诊断说某个弹奏者长于什么和缺少什么。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弹奏者应该自己摸索自己的道路,就像我当初摸索自己的道路一样。我认为一切艺术家都是这样形成的。1960年,与我的维也纳同行保罗·巴杜拉-斯柯达(PaulBadura-Skoda)和约尔格·德姆斯(JotgDemus)一起,我提出一项计划:高级班每年开课三周。计划的目标是让学生在一部作品上听见三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这样学生们就不得不自己下定决心选择哪种方式对作品进行阐释。但至少对较有天赋的学生来说,这将仅仅是第一步。他在以后得到的指教中将更多地是在音乐上自作主宰。当然肯定也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会把我们三人的意见汇合起来,并作出结论说什么地方三位老师说法一致,那就一定是真理。
我眼下还没有从事更多教学活动的计划。如果我有时间,我将更多地写作。《音乐的思考和后思考》最近出版了,但它甚至尚未开始说出我关于音乐的全部思考。书中绝大部分是一些讲义和文章的汇集。这些文章是多年中写成的,尔后又增补其它的文章来展开,阐明或反对我先前的看法。每篇文章均注有写作年代,这样读者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我思想的编年。既然它们并未囊括我全部的职业经验,它们不过是我愿意继续不断地说出的那些东西的一个开端。那中间有三篇很长的文章论述的是与贝多芬钢琴作品有关的问题,有一篇文章论及舒伯特晚期的奏鸣曲。有几篇小文章是关于李斯特的,有三篇小随笔是关于布索尼的,还有两篇是关于我的老师埃德温·费肖尔的。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与钢琴打交道)(C0pingwithPianos),它试图说明演奏者与钢琴之间的关系。奇怪的是这个题目以前几乎没有人写过。我试图说明钢琴本应怎样但却往往做不到这样,试图说明钢琴要怎样才能得到改进。从十多岁以后,我已不再继续搞绘画,现在只是作为一名观光者欣赏各地的风景名胜。参观和欣赏巴洛克(Barogue)建筑和罗马风格的建筑,已成为我一项主要的嗜好。
我的主要目标当然是继续弹奏钢琴。这一领域是如此广阔。还有许多作品我想与它们生活在一起,此外还有许多曲子有待学习。我将继续与贝多芬为伴,许多年前我就已经录制过他的钢琴曲。最近我刚刚完成一套新录制的贝多芬奏鸣曲、在此之后,我想更多地弹奏海顿的奏鸣曲,以及我先前从未弹奏过的舒曼的一些作品。例如,我还从未弹奏过《大卫同盟舞曲》(Davidsbundlertanze),而且我一直想弹奏他的《幻想小曲集》(Fantasiestucke)。我打算再加上斯美塔那(Smetana)的一些钢琴曲,这些钢琴曲很不公平地被人们忘记了。当然还要更多地弹奏布索尼,但不是他的协奏曲和《印第安幻想曲》(IndianFantasy)。这些作品不能令我信服。协奏曲是某一时期的作品——他的这段时期不会令我感兴趣。他的创作中有一段空白,在这段空白之后,他创作出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一开始是《悲歌集》(Elegies),总共七首,第一首是《转变之后》(NachderWendung),这首乐曲似乎表明他已意识到他的音乐正在发生一种裂变。在此之前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曲家,而现在他正在转变为一位富于原创性的作曲家。
今天的音乐和未来的音乐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一些很有地位的当代作曲家是我的朋友,虽然我并不弹奏他们的作品—我的曲目表止于阿诺德·勋伯格(Arnoldschoenbeng)和阿尔班·伯格(AlbanBerg)。实际上我的艺术趣味相当前卫。我不喜欢向后看的音乐,这种音乐听上去就像以前听过一样。勋伯格、伯格和韦本是伟大的作曲家。同时我也喜欢巴托克的音乐,尽管不太喜欢他最后的作品。我偏爱他离开匈牙利之前写的作品。我认为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优越于另外两首,我偏爱第三和第四弦乐四重奏甚于此后的作品。但这是我的祖父那个时代的新音乐。今后音乐会取什么方向我连一点最模糊的预见也谈不上。但我对此并不悲观。最近50年来,音乐美学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它们为什么就不应该继续变化下去?如果音乐又回到过去那些要素.那么它们必须在新的框架内重新发现新的东西。音乐会的节目安排也会发生变化,但那种像菜单一样的独奏演出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放弃。在李斯特的时代,节目是在乐队伴奏下混合安排的,一位独唱家和一位钢琴家同台即兴演出,一首交响曲的两个乐章被截取出来演奏,中间还穿插另一首独唱抒情曲以及其它风格各异的作品。我们很可能不会再回到这种时代,但有时候我也欣赏混合节目。在伦敦的普罗美纳德音乐会上,有一次我在管弦乐演奏中弹奏了《狄亚贝利变奏曲》(DiabelliVariations)。上一个演出季节里,我演奏了贝多芬的降E大调奏鸣曲(作品第7号),紧接着我又演奏了《合唱幻想曲》(ChoralFantasy)。
钢琴弹奏给了我极大的乐趣,但有时候它却是沉闷而艰苦的劳作,有些日子里我简直就讨厌弹奏!它变得需要我付出巨大的努力。也许是我感到身体不舒服,也许我疲倦了,或者仅仅是心情不愉快。天气可能很糟糕,而我有时会对气压的变化发生反应。有时是因为音乐厅,有时是因为我不得不使用的乐器,有时是由于节目的安排,有时则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事情。有些作品我从此不再弹奏就仅仅因为那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痛苦记忆。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记忆中总是保留着在那种极不愉快的条件下弹奏那些乐曲时的痛苦挣扎。因此我拒绝再次与这种沉重的负担交锋,除非我感到没有这些作品我就活不下去,那时便设法克服和战胜这些沉重的负担。似乎有一些艺术家把这归因于生物节奏。我却并不这样认为。另一些艺术家则依赖于星相学家的预言,他们按照星相学家对他们取得成功所作的预言来安排他们的重大演出的日期。这对我毫无意义,即使星相学家的预言真的很难,我也不想知道明天对我会发生些什么。如果仍然可能,艺术家就不能不奉献出他的演奏。他也许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去拼搏,但人生本来就是这样。这种演奏总是使我有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而在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和完美的演奏会之后,“我感觉到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清新。我没有自鸣得意的迷信,没有赢得好运气的魅力,不可能使上界的神明助我一臂之力。我宁可准备得更加充分。我的日常安排极为简单:排练之后,我通常小睡片刻;此后,在出场之前我弹奏半小时左右作热身练习以活动我的双手。我不能不稍作弹奏便走上舞台。这种方法对我十分有效。现在我把我每天练琴的时间限制在大约五小时左右,超过这一时间我会感到身体或精神上的不舒服。我相信除了弹钢琴以外。花时间思考和研究音乐是十分重要的。
这一职业之所以令我喜欢的另一原因是旅行。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很早以前便改变职业了。十二年来,我一直不停地到处旅行。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它充满企盼。我们的两个孩子还小。还没有到入学年龄,因此有时完全可以在旅行时把他们带在身边。但一旦他们入学,我便打算减少我的活动,特别是这种不断的旅行。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感到自己特别有幸是因为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它给了我许多乐趣,也给了我许多其它的东西。同样,它也给了我一种我必须追求的幻觉。因此,只要我还能够弹奏,我就会继续不断地弹奏。【完】
|
|
 布伦德尔(1931- )Alfred Brendel
布伦德尔(1931- )Alfred Brendel